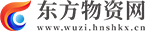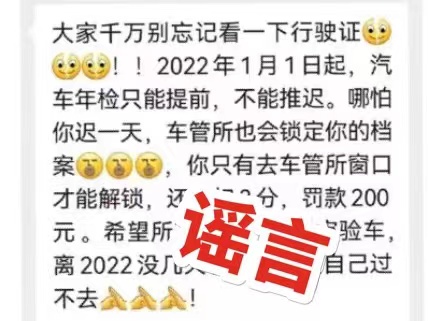新京报记者从西藏浪卡子县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获悉,8日凌晨3时许、7时许,中国著名藏族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因在拍戏时出现高原反应,先后在这两家医院接受抢救,抢救无效后离世,享年53岁。8日19时许,新京报记者又从万玛才旦弟弟处获悉,万玛才旦系心脏病突发逝世。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在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中,收录的第一篇便是与书名同名的短篇小说,小说里讲到“我”来自一个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机构,主要工作以抢救整理出版一些将要消失的民间文学作品为主。有一天,“我”请假来到村里找一位老人把之前没有采录的最后一个故事给录完。老人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但讲到一半,老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继续下去。结果,凌晨的时候,“我”接到老人女儿的电话,“阿爸刚刚走了”。在谈到这种开放式的结尾的设置时,万玛才旦表示,他觉得故事讲到一半突然停下可能会更加有意思,小说的故事内容和讲述形式都很重要,他执导的一些影片也是如此,比如,《塔洛》为什么要用黑白影像?《撞死一只羊》为什么要用四比三的画幅?现实和回忆为什么要有色彩上的区别?这些都是万玛才旦在电影表现形式上的探索。他还有太多探索要尝试。
万玛才旦在影片《陌生人》开机仪式上。
对万玛才旦来说,他热爱的电影故事也只讲了一半。去年11月,他编剧的爱情故事片《祝你旅途愉快》正式立项;由万玛才旦编剧、导演,黄轩主演的新作《陌生人》今年3月底刚宣布杀青;在今年4月底举办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万玛才旦担任了“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主席一职;在他去世前一天,他还在朋友圈“祝贺年轻的电影人”。他还有太多故事要讲述。
创造了藏族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这些年,万玛才旦在电影方面得到的肯定比较多,《静静的嘛呢石》(2005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寻找智美更登》(2007年)拿下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塔洛》(2015年)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撞死了一只羊》(2018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气球》(2019年)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椰奖……
不过,万玛才旦最开始是文学出身,这也与他之后执导的电影作品有很强的文学性有很大关系。他很小就喜欢电影,但当年高中毕业去专业学校接受系统的电影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经历就是先读文学,文学的爱好一直没间断过。他十几岁开始自发地写了一些小说,完全不是为了发表或者其他目的,也不知道写下来要干吗,有了表达的欲望冲动就写。他中专上的是师范,读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藏文化,而汉语是通过大量阅读文学来掌握。那时候上大学还是说方言,大家都不说普通话。
毕业后,万玛才旦当了三年的小学老师,当时读了比较多的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作品,比如鲁迅的作品等。他还接触了一些比较大众的作家,比如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在那个年代读这些书很是激动,一口气就读下来,有阅读的快感。他还通过一些国内作家的作品了解不同的创作方法,比如说荒诞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
不论是之后创作的小说,还是电影,万玛才旦创作的源头还是来自藏地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文化。
万玛才旦阅读了大量藏族文学,包含历算、梵文等很多学科。经典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读僧侣文学和民间文学,他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很大。比如民间文学喜欢重复的写作方法,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而藏族文学的经典作家很喜欢奇幻化或魔幻化的表现,它后面有很强大的佛教文化做支撑,比如经典的《米拉日巴传》就是这样。可能跟自己所处的文化宗教信仰有关,万玛才旦对荒诞派或象征主义的作品很感兴趣,更有亲切感,也更喜欢马尔克斯、卡夫卡这样的作者。
所以,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在写实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有一抹超现实的笔触和浓浓的宗教意味。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在茶馆的同一个场景同一个位置坐下,画面反映出两人的关联。
《撞死了一只羊》将拍摄地搬到了海拔5500米高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用镜头记录生命个体的情感和处境。该片用4:3画幅,并且用三种色彩对应三个不同时空,关于回忆和梦境的处理让影片十分写意。万玛才旦设置了三个时空,现实时空、回忆时空以及片尾的梦境。现实部分用了彩色,回忆部分则用了黑白,而梦境则用了一种类似油画的色彩。茶馆那场戏,每次老板娘回忆杀手金巴的时候,黑白镜头都做了虚化处理,故意模糊两个人的身份,制造一种梦幻、虚幻的感觉。影片《阿拉姜色》的藏族导演松太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对记者说:“这部片子可能是他以往所有的片子里面,最接近他文学气质的一部。”
电影《气球》中,两个藏族孩子将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耍,母亲卓嘎意外怀孕,爷爷突然去世,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认为是突然去世的爷爷的转世,在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孩子到底“生还是不生”,一家人陷入了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境地。
而他在小说中更是多次重复“生死轮回”的宗教命题。比如在小说《水果硬糖》里,一位藏族母亲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成为医生,一个成为活佛。在另一篇小说《特邀演员》中,一个剧组来到藏区拍戏,想邀请一位老藏民做特邀演员,但藏民以自己的影子留在照片上,将来死了灵魂得不到解脱为由拒绝了,但之后因为妻子生孩子需要钱,又同意作为特邀演员。
《塔洛》全片用黑白影像拍摄。
这些年,万玛才旦一直用文学和电影两条腿走路,文学滋养了他的电影,电影又反哺了他的文学。他执导的电影《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都是由他的小说改编而成,而《气球》则是先完成了电影剧本,又改编成的小说。
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曾称赞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族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对藏族电影人来说,万玛才旦是导师和伯乐
藏语电影的真正发轫之作,还是当时36岁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于2005年执导的《静静的嘛呢石》,此后十余年,万玛才旦扛起了“藏地电影”大旗,还培养了一众“后辈”,松太加和拉华加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于2011年导演了自己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随后又执导了《河》《阿拉姜色》,后者于2018年导演了处女作《旺扎的雨靴》,藏族导演的群像逐渐显露,开始形成一种气象,甚至已经有人将万玛才旦、松太加和拉华加等导演和他们的作品称为“藏地新浪潮”。但即便如此,“藏地题材电影”在目前的国内电影市场仍然处于投资少、题材过于单一的困境。
万玛才旦以“传帮带”的方式发展了众多“后辈”,将藏地题材电影从人迹罕至处和仰视符号化逐渐拉回到大众视野,令观众从平视角度更接地气地了解到藏地文化及藏民的精神生活。
万玛才旦先后就读于西北民族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他是中国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万玛才旦就读西北民族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作品曾经获得多种奖项。他的很多电影都改编自个人的小说,有很强的文学性。从2005年执导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他先后凭借《寻找智美更登》《塔洛》等反映现代藏民生活的优秀影片,频频在海内外获奖,为藏地电影赢得了广泛的关注。而对于松太加和拉华加等优秀藏族电影人来说,万玛才旦如同是导师和伯乐。
松太加比万玛才旦小5岁,据松太加回忆,两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认识了。因为都热爱文学,在地区文联组织的文学笔会上认识并熟络起来后,发现都喜欢电影,笔友开大会的时候,他俩就跑出去聊电影。有一年,万玛才旦去找松太加,说自己已经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了,建议松太加也去。
松太加至今还记得,当时万玛才旦领着他坐着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因为万玛才旦学的是编导,他就建议松太加学摄影,将来可以一起搭伴拍一些片子。松太加就在摄影系进修班学了一年,第二年跟着万玛才旦到文学系蹭了一年的课。藏地电影人这种传帮带式的精神在松太加这里得到了延续。已经独立执导了四部长片的松太加,现在有一个18人的创作团队,全部都是藏族年轻人,有高中毕业的,有大学毕业的,还有出家还俗的。松太加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写剧本,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很用功,也在关注戛纳(国际电影节),在聊这些事,挺有意思的。”
松太加(左)和拉华加(右)两位藏族导演在创作上都曾得到过万玛才旦的帮助。
拉华加在2005年的时候就知道了万玛才旦,“万玛老师当时拍了自己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轰动了整个藏区。”那时候电影在藏区还不是很普及,很多人对电影也比较陌生。2010年,拉华加通过哥哥认识了万玛才旦,万玛才旦建议他去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他建议我先去学文学,了解自己民族文化方面的东西”,之后拉华加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拉华加利用假期时间去跟组,最开始做导演助理、翻译、演员辅导等工作,后来到了万玛才旦《塔洛》剧组中就已经成为执行导演。拍摄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旺扎的雨靴》之前,拉华加跟了六七个剧组,《旺扎的雨靴》的班底也基本都是万玛才旦的团队,还有拉华加之前跟组时候合作的熟人。
寄希望当代年轻藏族电影创作者,多做类型尝试
藏语电影作品最近几年在国际各大影展很活跃,也获得一些奖项和关注,似乎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很有国际影响力的印象,但万玛才旦认为并不是这样,“这方面可能有一个误区,大家就觉得藏族本身的原因,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其实这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个跟在中国电影市场里面是一样的,放大到国际市场,它还是以电影本身为主。比如说一些电影节,它看重的是你作品的内容和声音,而不是看你的题材。现在涉及不同民族、各种不同文化的电影作品真是太多了,所以单纯靠一个题材想吸引眼球,希望有发行上的优势,我觉得很难,基本上不可能。很多电影节的标准肯定不是以题材为准,不会因为你是藏族题材就去选你。”
万玛才旦说,其实藏地电影很晚才出现,跟他们的整体处境有关系。好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电影制片厂,比如内蒙古有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新疆有天山电影制片厂,但整个藏地就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青海、西藏都没有,只有译制厂。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一些汉语电影译成藏语,在藏区发行。这里的电影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万玛才旦所著短篇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封面。
万玛才旦认为藏语电影因为处于刚起步阶段,它在内容的丰富度和类型的多元化上还比较欠缺,导演在创作的时候选取的题材就相对比较单一。比如《阿拉姜色》与《冈仁波齐》都有去拉萨朝圣的剧情,《皮绳上的魂》和《撞死了一只羊》都涉及了“复仇”与“救赎”的主题。
万玛才旦导演认为,首先要做一些类型上的尝试,这可能要寄希望于更多当代年轻的藏族电影创作者,因为他们年轻,在学习电影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对不同电影类型的兴趣。他从这两年的一些藏族学生短片中看到了这种希望。其次,要在题材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可以找一些既涉及藏地,又涉及内地的中间地段题材。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作者的转向,很多人也会问到万玛才旦导演将来有没有可能做藏族题材以外的电影,万玛才旦导演表示,“如果将来条件成熟了,也有感兴趣的题材,可以去做”。
2020年,万玛才旦在一次演讲中分享了自己学习电影、拍摄电影的一些经历,“时间的力量让我们成长,让我们逐渐明白很多的道理,逐渐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得耐住寂寞,必须得在时间中等待,等待机遇的到来。”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海报设计 刘晓斐
校对 刘越
关键词: